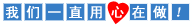日志
降上花不语
降上花不语
祁门二中 汤惟宁
4月30日,盟里组织活动去新建的黄山168国际徒步探险道(祁门段)考查,平时没有健身活动,自知无力去与身体抗争,还是努力一回吧!
不知别人晕车是怎么面对旅行的恐慌的,赶早进点食物,吃好晕车药,来到县委会门口(集中地)等车,抽着烟,排遣着登车前的紧张。
怎么同车的不仅是盟员?原来,是与祁门一中第四党支部教师及班子部门成员一块活动,一些老同事,突然这么近,一时都不知怎么嘘寒问暖,毕竟来自不同的世界,是曾经的独特性,是现实的适应性,是眼前的同事、政治身分。陌生后,产生的距离是一时难以克服的,相互间,都是基于历史的故事,只能瞬即相互回忆一下,以示认识,情谊还在。这个“在”的惯习,就是这样存在于人际间的。也如昨天被祁门的摄影家们硬拉到与市文联主席倪国华先生同席,没有故事、高潮,身份不配,彼此尴尬,不了解,不知怎么开口谈艺术、谈文化、谈美学实践。
共识于健身的祝愿,在一些日常或户外活动的参与中,人们相互传递着自身的身体情况或是间接地介绍自已的现在。一应一答的平等中,再知这些老(男)同事的意趣,或是一些不认识的年轻党员的风格,以及谈吐间的精神蕴涵与流露(表现);尤为感慨的是几位女教师的倦容,怎么努力地在脑子里搜寻,也难找回她俩青春的秀丽。也只能是,闭上眼,抑制住自已的倾听品性,在颠簸中调理气息安适着身体。
一来二往的吆喝声中,我们三十多人被安排在一个新修的农户家,人们可以想见其中的宽敞与明亮,也能感受到天高云淡茶季的阳光,与阵阵被风裹挟来的,混杂着泥土、衰草与花、茶的香,是沐浴,是香薰,还是洗礼……总之,是退劫了城里人身上的戾气。返朴,归真,还是还原,可以彻底放松自已,充分感知与这个世界上的事物的关系与距离。这里的鲜叶(茶)仍然要卖30块,户主人拿出他刚做好的新茶给我看,卖300元一斤,喝粗茶的我,只能用鼻子短促地猛吸几回,换位商贾,想瞬即领略这野山茶的品质。
顺着溪流进山了,绕过散乱的茶地,脚下的石路便开始支使着我的身体,需要跨跳,需要扶撑,需要稳步,需要平衡,……,渐渐地开始了深呼吸,汗珠也爬上额头,人们一再劝我脱掉的羊毛衫再也穿不住了。每到一个坳洼,人们便歇歇脚,拍照,抚弄着清凉的溪水,顺畅一下顶在嗓子眼上的气。再攀,队伍也拉长了,没有更多的力气说话(除非体力好的年轻人),安静了许多,自已也落在了队伍的后面,才觉形单影只。
低头看路,免不了会丢失眼前的风景,也是当我坐下喘气的时候,石缝旁的一朵紫色小花似是在向我点头示意,顺着她的目光抬头仰望,我便怜惜起这弱小生命的美丽,猛然想起人们乐道的“降上开花”与簇拥而热烈的油菜花海,是我“要”风景,还是风景“要”我?
仿佛与她处在洞穴中,形影相随,以至我再联想“洞穴之光”的隐喻,她与我,感知的是怎样的“同一”世界。也是昨晚与摄影师们的席间,我没有再侃印象派的口号——“光是绘画的主人”,以及后印象主义大师凡高的“介入”。
如果,我还愿与黄山市的文化名人(倪国华等)谈“艺术”,也是我有着长期看教学行为艺术的视角,有着长期的美学思考,也就敢在席间谈摄影家与生活的距离,谈“熟悉”,谈人文摄影作品中的叙事感、使命感,以及,为什么要“《干掉摄影师》”(我给夫人买的一本摄影书名)……;与倪主席的深入,也是我在席间谈凡高的“入境”,引发了他谈创作《迎客松》(作品)的独特思考与经历。有趣的是,他的话语中为了便与旁人听懂,用了个非常哲学化的词“解构”,接下来,再问“解构”——也就是,他是怎样把一个具有特定象征意味的精神符号——迎客松——进行主观重构(冒险)。可以说是在余音中,我俩又会去寻思“解构”的艺术表达(表现)困境了(在我看来,是生存美学的)……。旁边的“茶客”(摄影师)虽喝了酒,可能也只有他敏感到我俩的“清谈”之音。当然,更在于我们各自的艺术实践的困境。(在他们的世界是摄影艺术,在我的世界里是教学行为艺术)
不是油菜的花期,自然不是“要”去“看”油菜花,也联系到摄影们需要想清楚的“我要拍什么”(做什么事情,怎么去做)。怎么给自已的降上之行留个“影”,让我又想到倪先生的“叙述”,何不以“花”为题就此展开我的降上叙述呢?来降上的目的(或意义)与灵感瞬即形成了,无论山路如何,我便用手机一一拍下她们随着春风摇曳的身影,仿佛与她们对话之间写下自已的“降上花开”,而不是那些个千篇一律的,有关油菜花的(指向单一、明确的)宏大叙述。越拍越多,越拍越觉得生命形态的多样性、独特性,越拍越觉得这些并不起眼的小花是那么的神圣、神奇与绚丽。
“缘溪行,忘路之远近……落英缤纷, 渔人甚异之……仿佛若有光……”(《桃花源记》散句),队伍已走远了,过了几个叉路口,也没在意。忽听,身后有了声响,可能是另一群徒步者吧?还没弄清楚林子里嘹亮的童音来自何方,身后的山道上就蹦出个农家小姑娘,笑盈盈的,见到我也没见外,不惊慌,不好奇,没停步,似给后面扛着杉树的父亲引路一样,同样扛着一根杉树的妈妈紧随其后,她也只是见到身边有人(我),用左手的支肩棒撬了下右肩上的杉木筒,顺势抬了下头算跟我招乎,顾不了流在额上的汗珠,卷着热浪擦身而过。我还在纳闷他们怎么不顺山道放木下山,突然想到摄影师们的“要”,抓拍已迟,顺手按下快门,留下了她背包、扛木、急过弯道的背影。
与倪先生可以从容拍迎客松的背影不同,我已经回不到她抬起头的那一瞬,除非我是画家,可以再现,那也就是我无法创作出来的,独属于我的,心中的,降上的,女人花。
是体乏而缺少激情,是不专业没有艺术的技艺,因而无力表达“降上花开”的美,还是“花不言语”,我永远无法揭示(或实践)美的真谛。整理完手机里留下的二十二幅(花)生命形态,远不及这朵女人花明亮。与陶渊明不同,我内心里并没有那个世外的桃花园(或期待有整片的桃花林),也没受导(追逐)在油菜花海中自我沉沦。点点滴滴,通过手机的储存,我在努力构筑自已的“降上”(世界)。但总是不能完满。一种不能与事物、与世界对话的客观化恐惧向我袭来,当悲悯化成自我哀怜之际,舒婷的诗句在心头流过:“我是悲哀……是“飞天”袖间/千百年未落到地面的花朵。”
生命之花与我们共在,是我们视而不见,还是真的“从未落在地面上”?在一个缺乏语言、语境的世界里,总是需要诗人替我们说话吗?
说,教师“迪光”(借诸口迪光堂之名),我不是那些可以给别人光的人,或可以让某人灿烂的人。在我的手机(有限的关注)中,如果是生命的符号形态,也未必真是花的语言,但生命的顽强与美丽,仿佛总是在召唤着我。或者说,真是那句“上帝说有光,便有了光”,所谕示着生命的神圣与美丽。
重要的是去发现美,还是我们一直在自身的行为艺术中?舒婷在诗中,展开的是“人与神的对话”(“飞天”),历溪村的目连戏,有着“人与鬼的对话”,不同于现代戏剧要表现出的“人与人、人与事物、事情”的深层冲突与全面对话。然而,那些印象派大师们把审美对象直指农人、农舍、地头的艺术实践的召示,确是给人类文明的发展提供了极其宝贵的精神食粮。《晚祷》的静默,似是谕示着一件未完成的事宜。《降上花不语》,且当是我的生存美学实践的一次经历、叙述与思考。